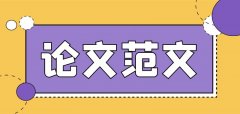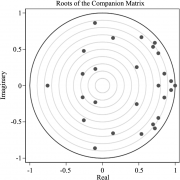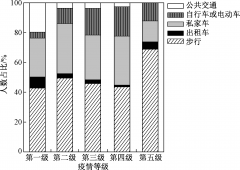熱門論文
最新論文
作為“反應裝置”的戰爭和作為“認知裝置”的“戰后” —為日本戰爭文學研究再尋坐標的嘗試
發布時間:2022-02-25 10:20
近年來戰爭文學(以日本侵華文學為主)的研究驟成學術熱點,從學術生態的意義上來說,這是 一個頗值得關注和深思的問題。一方面,戰爭文學研究作為一種類型文學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發 展環境和學術推動力;另一方面,我們的邏輯預設、理論工具和認識裝置之趨同又使該領域的研究出現 了不容忽視的“同溫層效應”。il) 如何 立 足 于已 有 的 研 究 基 礎 ,并 有 所 繼 承 和 詞 整 , 為戰爭 與文學相關研究再尋坐標,使之能在更廣闊的空間和關聯性視野中走向深入,進而具有更普遍的理論意義,是擺在研 究者面前的一個緊要課題。以下,筆者將結合十余年來對日本戰爭文學研究的一點粗淺實感與反思,以 及對國內外研究現狀的有限觀察,野人獻曝,從三個觀念維度提出問題,以期拋磚引玉,引發更為廣泛 的討論。
一、審美偏至、'`影子比較”與日本戰爭文學的世界坐標
在日本文學研究領域,昭和初期的文學雖未被開除文學史史籍、打入另冊,但其向來難成學界關注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日戰本后文學界的戰爭責任論爭及其思想史位相 ” (18AWW003)
[作者簡介)王升遠,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曙光學者,廈門大學校聘講座教 授,上 海 200433。
的主流亦是實情,而其中戰爭文學、國策文學更是長期以來備受冷遇的對象。例如,戰后初期為逃脫戰爭責任追究,很多文學家將自己戰時創作的戰爭文學、國策文學從書店中回購銷毀,導致了部分文獻的缺失;而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的相關評論、研究甚至全集編纂因“為尊者諱”而親親相隱,或因不 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敏感問題而三緘其口,遂使此類作品從后來者的學術視野中逐漸隱身潛形。事實上, 戰爭文學從文學史敘事中的隱匿除了受到文學政治學、文學社會學諸層面顯而易見的外部制約之外,還受到一個觀念性因素的阻滯一日本文學史被史家人為建構起的"脫政治化”和審美偏至的傾向。
早在 1957年,后 來 成 為 著 名 評 論 家 和 文 學 史 家 的 加 藤 周 一 ( 1919 2008 ) 就 曾 敏 銳 地 指 出 , ”所謂日本特有事物的概念中,日本特有的美的范疇大約是在江戶時代固定下來的,其內容主要以幽情、閑寂、淡泊等詞匯來表達。……從明治時代開始,這一方向與天皇制結合,擔負起一部分超國家義務的任務,并通過教育廣泛滲透到國民中。”©對于江戶國學家們為近代日本文學研究建構的民族基調,加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這種文學、藝術觀不適用于高度思辨的五山文學,也不適用于鐘情政治哲學和倫理問題的江戶時代的儒家文章,更不適用于在《今昔物語》中躍動、由狂言代代相傳,甚至對 江戶的川柳和雜徘句產生影響的日本民眾的活躍精神。”@加藤的不滿代表了戰后日本文學、思想重建潮 流中的開放派、國際派主張,意味著一部分文學家、思想家開始打破明治以降日漸走向極端的文化民族主義、國粹主義之秷桔,轉而將日本文學”一般化”,并為之尋求世界坐標。而其前提自然不是戰時閉塞、保守的政治文化生態中產生的所謂“世界史的哲學”這類對國際秩序的直白挑戰,而是試圖”重 建日本特有事物的概念,尋求普遍適用的衡量標準,這一嘗試也是我們尋求符合社會的唯一標準的嘗 試。”@他所強調的世界標準和民眾參與的意義,自然應置千占領時期結束、日本重獲主權、重返世界政 治舞臺的歷史文脈中予以理解。而這里亦應強調的是,超越江戶國學家們建構起的、明治以降又被不斷發酵、強化的文化民族主義觀念,在更為多元的框架和開放的格局中重審日本文學的特質及其世界意 義,是今人尤其是身在日本之外的研究者原本應有的學術自覺。
20 世紀是戰爭與革命的世紀,而 昭 和 初 期 的 文 學 ( 尤 其 是 戰 爭 文 學 ) 在 文 學 史 上 所 受 到 的 評 價 和關注不高,這自然是因為文學相對自律的發展軌跡受到了意識形態、政治權力的強力沖擊和宰制的結 果。無論是 1930年代新興藝術派與無產階級文學之間的論爭,抑 或 其 后 軍 國 主 義 抬 頭 后 對 前 兩 者 的 剿殺,文學遭受到的外部干預都是日本文學史上幾乎空前的異態。隨著戰爭的爆發和戰線的擴大,無論是主動迎合抑或被動卷人,文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裹挾進時局,文壇生態因此而劇變。時局之下,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參與,對國策、戰爭的抵抗抑或“協力”,都使得“作家"淡出@,“知識分子"凸顯。因此,以“無美”抑或“乏善”之名觀察、總結極端語境下、異態時空中的文學,總會給人緣木求魚 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昭和初期文學史幾可視作一部極端語境下日本文學家、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求真”也應該成為我們重審這一時期日本文學史的重要認知維度。若不能調整既有的文學史觀,不能正 視昭和初期、戰后初期文學的文學史意義,我們就很難在歷史繼起的意義上為大正文學與戰后文學建立起一個具有連貫性的邏輯與線索,文學史敘事也將因此喪失歷史性。
正如錢穎一教授在其《“比較論叢" 序》 中引用的美國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李普塞特 ( Seymour Martin Llpset, 1922 - 2006 ) 那句話名言一 “只懂得一個國家的人,他 實 際 上 什 么 國 家 都 不 懂 。”氣 比言對于日本文學史、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同樣適用。坐標意識、參照物意識對于我們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 斷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說在“紅色的三十年代”,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是全球無產階級文學浪潮中的 有機組成部分(事實上,學術界至少己對中日無產階級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做了較為充分的研究),那 么,對于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日本之“戰爭文學”“國策文學”等類型文學也可以以在法西斯主義肆虐全 球的“極端的年代”中的德、意兩國此類創作為“影子比較"的參照系,從而在更為普遍的意義上求 得政治與文學、暴力與文明、戰爭與人之復雜關系的最大公約數,為人類面對大規模、集團性暴力的因 應模式及其文化思想表達沉淀出有效的歷史經驗和研究范式。美籍日裔學者橋本明子以德國的戰爭創 傷、戰爭記憶為“影子比較“對象,討論日本戰敗后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相關諸問題的研究,堪 稱典范。她指出:
作為一本在全球“記憶文化”背景下評價日本個案的書,我的分析還采用了“影子比較“法, 批評性地運用了從探討其他社會艱難記憶和文化創傷的著作中產生的概念和觀點。由于此類針對德國記憶的批評性著作廣泛、多樣、全面,所以我會經常借此來闡釋日本的一些模式,通過間接或直
• 60 •
接的比對,來洞悉各種意義的內涵。… 其他對日本個案有所啟發的比較,包括了“一戰”后的
土耳其、越戰后的美國和后共產主義時代的中歐。通過這一比較方法,我得以對文化創傷在不同戰敗文化中的意義進行觀察。。
在日德比較的意義上而言,荷 蘭 學 者 伊 恩 . 布 魯 瑪 ( Ia n Burnma, 1951— ) 的《罪孽的報應:德 國
與 日本 的 戰 爭 記 憶 》 作 為 一 部 政 治 游 記 p( olitica l tra velog ue ) 對戰后兩國不同的悔罪方式進行了富千洞
見的觀察。正如徐賁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瑪通過他的政治游記要表明的是,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不是 其種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質特征,而是政治結構。對德國和日本戰后悔罪起到關鍵影響的,是兩國戰后不 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過程。”©事實上,下列學術課題均是極為重要的:如日德兩國戰爭時期(尤其是總體戰體制下)的文學生產出版與傳播、文學家的時局因應策略、流亡文學以及“內心流亡“文學、言論空間喪失語境下的“潛在寫作"、對英美文學與思想的批判與抵制、戰后盟軍對日德的文化思想改造、戰爭體驗與戰爭經驗對戰后文學和思想的深刻塑造與影響、創傷文化以及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自由派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之間復雜的三元關系氣者問題的比較研究等等,均有待學界進一步 發掘、拓展。@從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的意義上而言,此類研究有著天然的可比性自不待言,更重 要的是,當我們以更為開放的觀念和視野討論戰爭與文學、文化的關系問題,那么,基于一國文學內部 的考察、僅限于有限作品考察而缺乏對相關文獻更為廣泛的占有、缺乏對相關人事關系必要考證基礎上形成的所謂國民性日本文化某些特性決定論乃至文學家良知論(這一點后文將有進一步的展開)之類的結論恐怕就會站不住腳-這是一種擒住了猶大而放過了總督的思路。
有著審美價值的文學經典固然值得銘記,然而,給全人類帶來過巨大創傷、至今余痛猶在的特殊時 期文學與思想,文學被政治全面侵襲和宰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淪為政治之附庸和幫兇的時代作為一種歷 史“教訓”也不應被遺忘,甚至更值得我們以“人"的名義省思和銘記。為此,筆者嘗試以“魚缸文 學史”和“江湖文學史”@的觀念(當然,二者并非互無牽連的二元對立關系)調整我們面對“美學意 義上諸神流竄、文學被放逐的時代”之打開方式,如此,則那些”被以單純的審美原則為由拒斥于傳 統文學史敘事之外的失蹤者們(例如戰爭研究視域下的殖民地文學、宣撫文學、返遷文學、戰爭文學 等,抑或旅行文學等非虛構類型文學等)將被激活,從而成為沖擊既有文學史定見、定論的學術、思 想資源”。@
二、作為“認知裝置”的戰后
近年來,中國學界圍繞戰爭時期日本作家涉華活動、言論和創作做了大量研究,有力地推進了戰時 中日文學關系的研究,這也是近年來中國中日文學關系研究的有力增長點,“中國視角”的參與、介入 提供了作為戰爭受害方的獨特立場與視角,相關研究也極有必要穩步、長久地推進下去。但僅有對 “戰時”的關切和“中-日“雙邊闡釋框架恐有不足。首先,回到學術研究的疆域中來,就日本文學 史、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唯有帶著“戰前-戰中-戰后"貫通的視角,才可能建立起具有歷史連貫性 和邏輯自洽性的作家論。日本近代文學從相對自立、自律發展直至淪為政治附庸,日本言論空間的逼仄 化是明治以降漸進變化的歷史過程,作家的境遇與抉擇也隨著時代潮流的劇變產生了巨大的振幅,高頭 講章中的主義、情懷與艱難時世中的現實應對往往背離。戰后初期日本文壇的戰爭責任論爭中披露出的 種種作家戰時行止便已為我們提供了諸多鮮活的文學史例證。甚至時至 1954 年、1957 年, 日 本 還 至 少出版過兩種對日本文化、思想界一些重鎮學者戰前、戰后言行不一的”事大主義“行止一一指名、并 提出尖銳質疑和批評的文集。@其中,青野季吉、阿部知二、潼川鶴次郎、伊豆公夫等作家和評論家的 名字都赫然在列。小熊英二的《“民主”與“愛國”一戰后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所強調的便 是這樣一種“貫戰史”的視野,凸顯了“戰爭體驗”對于日本戰后思想無遠弗屆、甚至堪稱決定性的 影響。叮同樣,戰后日本思想界的諸多重要理論問題一諸如“轉向”問題、主義/路線與現實的關系問 題、文學家道德問題和戰爭責任問題、“實感”問題、主體性論爭、戰后日本文學領導權的爭奪等一一 都要求我們帶著自覺的歷史化觀念,將視線投向戰時、戰前甚至是明治以降的近代史整體,將文學家戰 時的活動、言論和創作置于歷史繼起的語境、狀況和脈絡中加以辨析和判斷,非此則將無法理解其思想 根源與戰后余響,無法把握戰后文學與思想的源流,更無法在貌似劇烈變動、前后相悖的言論、抉擇中 發現其深深地貫穿始終、不變如一的潛流。事實上,今人在戰爭文學研究中處理的諸多理論問題在戰后
• 61 •
初期日本文學界、思想界的戰爭反思中多已有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只是這些幾乎都被研究者們有意無意地繞過去了,這是不應出現的"盲點”。若我們不能同時將這些文獻予以“對象化”,則非但難以在學術史的層面上有效地“接著說”,更難以在思想史、政治史的層面上理解、把握戰后至今日本的政 治、思想流變脈絡,文學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作為一種歷史敘事也將因此喪失"鑒今”之功能,這是 頗值得警惕的。
“戰后”是一種(階段性)結果已知的狀態,若能將“戰后”(尤其是“戰后初期”)不作為一種 ”后設立場”而作為一種類似于后視鏡一樣的認知裝置,那么就將深刻改變我們單從空間維度意義上的中國視角、亞洲視角提出問題的慣性思維,以一種時間維度重新審視戰爭與日本文學、思想、社會的過往,值得我們以其為中心反復進行貫通式的思想操練,在“知其然”的基礎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將若何"。當然,對戰后作為一種時間維度上后視性認知裝置之意義的強調,并不是否定了空間層面的雙邊抑或多邊的問題框架,他們的交錯會衍生出更多有學術價值的問題,從而對我們的既有的歷史想象形成更多實質性的沖擊。以“滿洲返遷文學”研究為例,我們就有必要超越就返遷文學文本談返 遷問題的思路,把視野前移。簡單說來,就是沒有“大陸開拓",何來“滿洲返遷",只有把“大陸開拓文學”與“滿洲返遷文學“視作因果鏈條而非分而治之,才可能超越因果分治的研究格局,構成對 東亞殖民主義及其危害更為深入的觀察與批判。
落實到日本文學家戰爭責任的研究,其情亦然。在戰后初期的戰爭責任討論中,論者大多取了 “內向化”的批判視角,旨在批判戰爭文學創作者對本國文壇墮落之責任,及其栽害青年、毒害民眾的惡劣影響氣而對這些文學家以亞洲諸國為對象、煽動敵意、美化侵略戰爭的活動、言論、創作之關注 與批判則殆近于無。文學家在這場以亞洲諸國為對象的侵略、殖民戰爭中之行止,卻以以本國為對象的“內向化”總結告終,盎盂相敲,一地雞毛。將戰后日本文壇戰爭責任論爭的討論文本,與對戰時日本作家以亞洲諸國為現場的文學活動關聯起來,將為前者補全其缺失的“外向化“視角。以上兩例皆是 戰后作為認知裝置的”時間維度”與中-日、日本-亞洲的空間維度相互交錯的產物。
當然,中-日、日本-亞洲的雙邊思維框架也有必要進行更為細致的辨析。日本對“偽滿洲國”、華北淪陷區、蒙疆偽政權以及華中地區等的滲透和殖民統治存在著共時意義上的差異性;同時,已被并人日本版圖的朝鮮半島、沖繩等地也因歷史源流等問題成為與中國和日本帝國之間無法”一言以蔽之“ 的存在。這些因素之間的不同排列組合關系,在另一個次元上會衍生出更多復雜交錯、頭緒紛繁的雙邊抑或多邊問題,對其追問將增進我們對戰時“中-日“雙邊文學、文化關系框架之內在多元性、復雜 性的理解,豐富我們對戰時歷史的想象、拓寬學術闡釋的空間。
三、作為“反應裝置”的戰爭
在既往的戰爭文學研究中,單一的作家論往往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 研究者大多不可避免地將歷史狀況外、后設立場下今人之道德判斷過度投射、滲人到研究對象上,導致相關論斷的非歷史化、主觀化。故而,我們除了應為日本的戰爭文學建立世界坐標之外,亦須在同時代日本文壇內部建立起擠輩間可資參照的坐標。換言之,對戰時文學家的活動、言論和創作,不僅需要一個相似政治語境中的國際參照物,更需要在同一政治語境、歷史文脈中的同時代參照物。
戰爭與文學之關系中的諸多判斷,關 乎 文 學 家 的 戰 爭 責 任 問 題 ,按 照 雅 思 貝 爾 斯 ( 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 的罪責劃分,則 至 少 應 承 擔 道 德 責 任 和形 而 上 的 責 任 ,因 此 相 關 論 斷 須 兼 顧 實 證考 察 之 深 度 ,以 及 對 其 時 文 壇 狀 況 觀 照 之 廣 度 戶 自 1946 年 1 月 1 日 小 報 《 文 學 時 標 》 在 “ 文 學 檢 察 ” 欄 對 40 位 日本文壇大家逐個揭批起氣 從身陷圖閣 18 年的德田球一、宮本顯治,到 流 亡 海 外 的 杉 本 良吉,從戰時離群索居、不合作的永井荷風,到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搖旗吶喊的保田與重郎、佐藤春夫, 日本文壇的大部分有聲望的作家都在“戰爭責任“追究的風潮中被一一公開論罪過。人們試圖揪出并 清除戰時文壇的"害群之馬”,為戰后文壇激濁揚清、除舊立新。這其中固然夾雜著公憤與私怨,以及“明治一代”和“大正一代“爭奪戰后文學領導權的私念。可同時,當作家們不愿被提及的往事被一一揭批于陽光之下,作為后來者的我們或許就能據此描繪出一道漸變的光譜——文學家在戰時的反應是復雜、多樣的。而歷史研究所必需的“同情之理解”(這并不意味著要為相關責任者脫責)要求研究者須在歷史語境和時代狀況下,在活動、言論、創作的三位一體的認知框架下,在公表作品與私密寫作的有
• 62 •
效融合中,考察在戰時極端語境下文學家時局因應的多樣性問題。筆者想以氯氣與金屬間的化學反應為喻展開討論,當然,文學家實際反應的情形要比此遠為復雜多樣,這里只想提示一種認知模式。
在這個“實驗”中,我們不妨將戰爭比作加熱裝置一煤氣燈(不同于酒精燈之處在千它能提供 更高的溫度),將戰時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政治氛圍比作氯氣,以此來測試身處其間的日本文學家之“活 潑性”。金屬鈉在無須加熱的狀況下,遇到氯氣即可與之發生反應,這就很像大正、昭和時期日本文壇 操盤手菊池寬。永井荷風就在其日記中對菊池敗壞文學、出版兩界風氣的惡行極為不滿,頗多指摘。@ 而鐵則不同,它與氯氣之間在不加熱時緩慢反應,而加熱的清況下則會劇烈反應。毋寧說,這就像戰時 大部分文學家的境遇和抉擇。當然,也有銀這般金屬,不加熱不反應,加熱后緩慢反應,中野重治則屬 于此類作家。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后不久,中野便因時局的變化放棄了其一貫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走上了 國家主義道路。@而最可貴的是金,無論如何加熱,它與氯氣之間都不會發生反應,這就類似于永井荷 風、谷崎潤一郎、正宗白鳥、志賀直哉等為數極少的幾位疏離時局和戰爭的文學家。對于日本文壇而 言,戰爭成為了一種無可選擇、也幾乎無法逃避的反應裝置,日本人、日本文化被人為建構起的本質主 義論述(諷刺的是,這毋寧說這正是昭和軍國主義對外宣傳的主要論調),日本文學家被今人期許的道 德良知等無不要經受非常態的酷烈考驗,并在這一過程中“原形畢露"。當然,戰后一度在戰爭責任追 究中風頭占盡的“大正一代“青年評論家也因戰時未到須經受道德拷問的年紀而遭到前輩們的反詰。 將戰爭作為一種極端語境、一種反應裝置、一種透視法,重審戰爭中的日本文學與思想,便可進一步拓 寬戰爭之千日本文學史、思想史的意義空間,甚或超越日本而更具普遍性意義。當然,對文學家境遇與 抉擇的多樣化分布也提示我們,在認識論層面存在著對戰時日本文學家做群體性描述和單論之外的第三 條認知與闡釋道路。這也會讓我們理解,那些一度在戰時走向巔峰、又在戰后初期被打破的文化本質主 義論述從 1970 年代開始何以又卷土重來,成 為 文 化 潮 流 ,其 背 后 暗 含 著 怎 樣 的 文 化 政 治 問 題 。
當我們將文學理解為“人學”,那么對“文學"的狹義理解常使我們的戰爭文學研究顯得不夠“文 學”。如果說戰爭文學是“極端語境下的文學”,那么戰爭中的文學家,自然也是“極端語境下的文學 家”、“極端語境下的人",而這卻是常被我們有意無意間無視的層面。在戰后的戰爭責任論爭中,文學 家既是“國民靈魂教師”、亦是“國民/市民”這一身份的雙重性@曾一度成為討論的焦點。文學家與常 人共有的市民身份亦是我們的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問題點,而這對千文學家戰時的抉擇而言,卻是不可小 視的判斷維度。近來歷史學界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學術動向。侯旭東在《什么是日常統治史》也呼吁 ”重返人/事關系的歷史世界”氣而這些正是“常事不書”的史學傳統中被抹殺和遺忘的部分;王汛森 感嘆歷史敘事中“人的死亡",他是在對歷史人物或團體苛責等意義上呼吁“人的復返"的氣這讓筆 者想到了阿倫特,她在《人的境況》中甩開了極權主義這一倫理秷桔,繼續思考個人倫理責任與政治 生活之間的關系問題,認為即便在自由制度之下,人的個體責任依然是第一位的。落實到戰后日本的戰 爭責任追究上,若僅將罪責落實到一部分“結構性力量”上,無視更多相關團體、個體的責任,則終 將架空”責任",使之無法落實。事實上,戰時包括文學家在內的日本人日常生活當然也是在軍國主義 制度與惡劣的生存環境結構中得以展開的,因此我們更需要前述“江湖文學史”的視野。
舉幾個例子。1956 年,文 學 評 論 家 荒 正 人 在 與丸 山 真男 、 鶴 見 俊 輔 、 南 博 等 討 論 戰 爭 責 任 問 題 時 , 談到了一些作家在戰時的復雜心態:
《文藝》雜志的八月號中,伊藤整和高見順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一個對談,很有意思。大家 都擔心征用令是否到來,伊藤整和高見順都以為會來,結果伊藤整沒收到而高見順卻收到了。高見順在學生時代參加過左翼運動,因此他很擔心戰爭爆發后自己會被拘捕起來。征用令來時,他慶幸自已被征用去了南方,只要不入獄就好,總算松了一口氣。他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奇妙的原因去了南方,卻完全不知是緬甸戰線戰況若何,他說自己以從軍的名義與被征召入伍的士兵們走在一起時, 有了這樣的感想。
大家都拿著一張紅紙來了,拼命努力。這樣一來,盡管對戰爭有些不解之處,但大家都辛苦之
時我也在辛苦著不挺好嗎?此事暗示了很多事情。不僅是高見順,就連像佐多稻子那種有著明確的無產階級作家意識的人,也有與士兵同甘共苦的心情。戰后,這被很多人以其做了不好的事情為由而追究,關于這種痛苦,佐多女士自己多有撰述。我想這呈現出了一個文學家戰爭責任在其戰后自 覺的形態。@
·63 •
這種狀況是極具代表性的。它這意味著極端語境下、群體中文學家天人交戰之際的兩難心態。在高 見順那里,較之千因左翼運動被捕入獄,從軍或許是更好的選擇;較之于特立獨行,從眾或許是更好的 選擇。。
再 比 如 , 1946 年 ,年 輕 的 評 論 家 小 田 切 秀 雄 在 其 起 草 的 《 文 學 領 域 戰 爭 責 任 的 追 究 》 中 將 六 類 文學家列為目標群體,其中也包括“抓住機會四處奔走,通過特高警察、憲兵或其他力量使批判自己的 人陷入沉默者”和“向特高警察出賣、密告、挑撥,污蔑自己在文學上的敵人乃`赤色分子'或'自 由主義'之徒"。兩類。如前所述,我們可以以戰后為認知裝置,從戰后文學界提出的諸問題反觀戰爭 時期日本文壇狀況,方可理解昭和初期結構性力量與“人”的作用之間微妙復雜的關系。
而“國民靈魂教師”與“國民/市民“雙重身份,在一些私文本中得到了彌合。盡管“人類為了讓自己活下去,確實會適時替換掉自己的記憶" (鶴見俊輔稱之為"`揉搓'感情”)。,甚至有時,連日記都不那么可信。野扳昭如在討論“日本人和日記”時亦坦言,“無論出千怎樣的動機,要真實地寫出自己的心情,即便不說謊,也會出現一些不確定的敘述。自己既是寫作者,又是讀者,在無意識當中就會出現歪曲。心但我們似乎亦須承認,日記雖未必有著前后自洽、一以貫之的“義理”,但其間貫流的“人情”、精神卻有著不容小視的價值。就像筆者在《跨戰爭視野與“戰敗體驗"的文學史與思想史意義》一文中所強調的那樣,日記中的體驗性、情感性是對抗玄虛、迂遠的日本式新民族主義、美化戰 爭論調的重要武器。佐高信在與加藤陽子對談時談到了日本反戰運動的缺陷,他犀利地指出,“學者總想要依據井井有條的邏輯來講述`反戰'。但是直接表達出他們厭惡戰爭而騷動不己的心情,甚至不惜撒謊來逃避兵役的心情,難道不好嗎?我感覺如果學者不從這里開始講,就很難成為廣泛的`反戰' 運動。”。 而 這 ,也 是 戰 后 75 年 之 際 ,我 們 重 讀 作 家 戰 爭 日記、戰敗日記的旨趣和意義之所在。
高校學術論文網提供專業的碩士畢業論文寫作、博士論文寫作發表、碩士論文寫作發表、SCI論文寫作發表、職稱論文寫作發表、英文論文潤色的服務網站,多年來,憑借優秀的服務和聲譽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好評,為畢業生解決寫論文的煩惱
高校學術論文網提供專業的碩士畢業論文寫作、博士論文寫作發表、碩士論文寫作發表、SCI論文寫作發表、職稱論文寫作發表、英文論文潤色的服務網站,多年來,憑借優秀的服務和聲譽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好評,為畢業生解決寫論文的煩惱
上一篇:新冠肺炎疫情對金融業的影響及后疫情時代金融治理體系研究
下一篇:鴉片戰爭與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戰爭比較研究 ——-以軍事素養、國民性與交通為中心的考察
相關標簽: